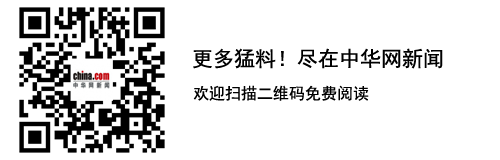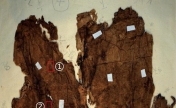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中华读书报》(《利用古籍受阻北大学者述说困惑》20050323,第1版)、《南方都市报》(《“苏图事件”:谁限制了一个学者使用善本的权利?》20050328,B08版)相继采访与报道了“苏图事件”,即笔者与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相商复制或钞录清季学者曾文玉《汉学师承续记》稿本事经过。因为此前只有我的“一面之辞”,而苏图方面未有表态,加上网上议论,纷纭驳杂,所以我再未发表任何意见,对采访者一律回绝,对来信者则全部回复。现苏图方面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此事也不再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正如网友们所言,我国目前存在的古籍收藏与利用之间的矛盾,的确不仅仅是苏图之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古籍的“藏”而不“用”,或者“可用”而有“高价”,严重阻碍了古籍的利用、整理与刊布,使其成为物化了的古董,而失去了文化传播载体的作用。本文将针对这一现象,进行详细的例析,并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与建议。倘拙文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对古籍收藏单位的改革起到点滴推动作用,则是本文真正目的之所在。
●古籍:“藏”而不“用”形同废纸
在我国目前尚没有《图书馆法》,对于古籍的收藏与利用,诸馆各行其是,无有定规。因此,我们在此以《著作权法》与《文物保护法》为参考,来试图讨论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古籍收藏单位与读者各自对古籍有何权利;二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籍这类特殊的文物,也就是说究竟是“藏”大于“用”,还是“用”大于“藏”。
谁都知道,著作权属于作者,作者享有著作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也就是说作者有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从完全意义上说,无论古籍收藏单位与读者,都不拥有古籍的著作权亦即版权。但因为公共图书馆属于国家所有,保存于此的古籍,也就具有了国家重要文化财产的自然属性。在此基础上,我个人认为图书馆所能做的就是保护古籍的作品完整权,也就是说拥有古籍实体形态的保护权(不是垄断权与占有权),并代表国家行使古籍的财产权。因此他们有责任使古籍得到良好的保护,不至于损毁与流失,然这尚不是《著作权法》中作品完整权的内容(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同时,古籍收藏单位在必要时,还可经有关部门批准后,通过合法程序拍卖古籍来筹措经费等。当然,因为古籍收藏部门为近水楼台,因此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优先使用权,也就是复制、拍照、整理、研究与发表的先得机会。
但是从读者的角度而言,联合国《公共图书馆宣言》称“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是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和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又称“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我国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也称“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即便是《文物保护法》,也明确称“复制、拍摄、拓印馆藏文物,不得对馆藏文物造成损害”。这些法规都没有规定不能复制,相反是主张复制与利用的。照我个人理解,就古籍而言,任何人都有阅读古籍的权利,都可以编辑古籍的内容,并出版发行,且享有该书的“编辑著作权”。
那么,在何种情形下,古籍收藏单位可以拒绝读者阅读、钞录或者复制古籍呢?窃以为在下列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的:其一,古籍因年久失修,已到触手即碎的程度,在尚未修复或正在修复中;其二,古籍因展览等原因,正在使用过程中;其三,因阴雨天气、湿度太大等原因,阅读古籍将对该书造成损害等。但这也都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理由而已。
我们再来论古籍与文物的关系。《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包括“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这其中当然包含善本古籍。但古籍是文物中的特类,即其基本功能是一部书。可是在我国的现代图书馆里,一些管理者却忽视了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从书的本质角度讲,古籍与我们手里的一本普通书没有任何区别;但由于其又有文物的属性与价值,因此便与普通书有了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为了保护其不被损毁与遗佚,所以不能买卖,不能借出,不能撕毁,不能批改,不能无数次地复制与拍照等。但这一切保护措施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也就是供读者阅读,供学者整理、研究与发表。正如《南方都市报》采访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林子雄先生所言:“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文物保护法》也主张“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如果将古籍当作不可触摸的文物来看待,就完全违背了作者著书是为了传播与流通这一初衷,也使书籍丧失了传递知识这一基本功能,同时也与《文物保护法》等的法律精神相违背,而物化了的古籍也就只成了缥缃紧裏、高束锁钥、遮灰蒙尘、虫蛀风蚀的废纸而已。
退一步讲,即使把古籍完全当成物化了的文物,其整理与出版,也丝毫不减其文物属性与价值。因为无论是影印出版还是点校出版,该部古籍的实体形态仍完好地保存在收藏单位,并不因为其书的整理而丧失其文物性。而且在整理出版后,在一般情况下原书便不再轻动,相反更有利于古籍的收藏与保护。
国外有些图书馆对善本书的复制,基本上是全本复制,但最后数页不复制,只可钞录,这样既方便了读者,又保留了馆方拥有版本的完全形态。
●古籍善本:一个数学符号式的“无穷大”概念
何谓善本?简言之,善本就是一部好书。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讹误相对最少的书籍。一部书愈往后世,流传愈稀,于是古籍就有了文物性。清末张之洞给善本提出三个标准:足本(无残阙无删削)、精本(精校精注本)与旧本(旧刻与旧钞)。在今天意义上,我们一般把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古籍称之为善本。学术界习惯上将乾隆六十年(1795),定为区别善本与否的时代下限。对于学者来说,则更注重是否精校精刻、装帧独特、套印精美、图像生动、书画绝伦等,也就是其书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但一般而论,一部古籍凡具备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之一者,就称之为善本;倘一书而三者齐备,当然就更成善本中的善本了。
对于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来说,一般国内稍具规模的大学与研究单位,常用的古籍都是具备的,需要外出查的书,多是不常见的古籍。而如果一个学者下了很大的决心,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北方,或者反之,他所奔往寻觅的,毫无疑问是不得不看的、寻常难见的、甚至是该馆独存的善本。本来,什么是善本,完全不必强求统一。但在有些古籍收藏单位,“善本”的外延,却如数学概念中的无穷大式符号,蔓延而无际。因此,当读者到古籍收藏单位阅览古籍时,就会发现几乎你要看的书,差不多都是善本。
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古籍一旦成了善本,就意味着两种改变:一是其收藏与保护的待遇会比一般古籍高,这是大大的好事。二是一旦成为善本,就与读者拉开了距离,借阅的难度随之加大。这其中又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将善本书视为“闺中处子”,既不可看更不可动。这种现象在一些藏书少但偶有数种稀见善本的图书馆最为常见,比如笔者在参与整理《全宋诗》的过程中,曾整理过宋代诗人杨万年的《裨幄集》,是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删改太过,我查到北京某高校藏有旧刻本,前后跑了四趟,最后请其馆长特批,才准许对校,但具体负责的一位女老师让我在门外等着,由她去替我对勘,使我哭笑不得。第二种是“半遮半掩”,可以看但不可以全看,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恕不举例。第三种就是笔者在苏图遇到的情况,可以全看但不可以复制,甚至不允许全部钞录。
更为严重的是:善本与巨额的所谓“底本费”一旦结合,“善本”就由一个可爱的名词,变成了学者谈必色变的恐怖词汇。
●巨额底本费:横亘在读者与古籍之间的天堑
在我国各图书馆中,善本的底本费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每页数元,现在已经涨到每页动辄上百元。凡收取底本费的古籍收藏单位,一般而言宋元版书每页大都在百元以上至二百元左右,即使是清季稿本、钞本等,也每页在二三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普通古籍,从清季书籍每页三四元至清中叶每页七八元亦不等。如果是想对一幅古画拍照等,则每拍在数百元甚至高达千元以上,量物论价,无有定说!
笔者在国外一些图书馆也复制过中国古籍甚至是善本,所收只是极低的费用而已。我们且不用与国外比较,据笔者了解,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收费方式为“善本图书复印及一般复印,计费方式(A4一张1.5元、B4一张2元,A3一张2.5元)。微卷复印一张3元”。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的收费标准为“A4与B4纸,每张新台币2元;A3纸,每张新台币3元”。
我们如果将人民币与新台币折算一下(1元人民币约合4元新台币),以复制或扫描一张黑白善本件A4纸为例,台湾各馆中收费最低的一张仅1.5元台币,合人民币约0.40元;最高者也仅一页15元台币,合人民币约4元。我们内地所收取的底本费,与海峡对岸相比,差价竟在数十倍甚至百倍以上!难怪台湾学术界的朋友常抱怨说,内地图书馆收取巨额底本费,不仅于情于理不通,而且是一件让他们极其扫兴、极伤感情的事情!我国著名《水经注》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曾疑惑地问:“中国人在国际运动场、游泳池之类的地方很懂得要为国家争点颜面,至于包了飞机到处参赛,用高薪聘请洋教练等等,也显得出手大方,风格可嘉。但在图书馆这样重要的文化事业上,为什么不想为国家争点颜面、表现一点风格呢?为什么老伸手向那些阮囊羞涩的知识分子和研究生们要钱呢?”(陈桥驿《郦学札记》第362-364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陈先生的疑惑,我想也是广大读者的疑惑。
因之,巨额的底本费,就成了横亘在读者与善本之间的一道天堑!在很多装修精美的图书馆善本室,桌椅古朴,窗明几净,但读者寥寥,门可罗雀,因为有很多读者望书兴叹,知难而退了。
●进退无据:古籍整理与研究者的困惑
古籍整理与研究,是一项貌似与现实社会无有关连,而实际上与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事业。在我国历史上,如西汉末刘向父子校理群书,东汉郑玄等人遍注群经,魏晋隋唐间诸经义疏之作,宋明时期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的编纂,都是一代盛事。而清乾隆朝官方整理《四库全书》与民间考据学家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更是一度成为“显学”。也正因为历代学者与政府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古籍,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期,由于战乱频仍,国势危殆,古籍整理与研究自然不可能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也很重视古籍整理与研究,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单位,专门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今天整个社会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却处在进退无据的狼狈境地中。众所周知,在我国的高校与科研单位中,“重理轻文”是久已有之的现象;而在人文学科中,古典文献专业又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凡国家与各高校及科研单位,一旦涉及到专业的裁撤、学位点的变动、机构的合并等,首当其冲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就是古典文献专业与古籍研究所等机构。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所面临的至少有“五难”:即职称提升难、人才培养难、项目立项难、成果出版难、成果获奖难。我们在此,只就与本文主题相关者论之。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像国家社科基金与各省市、各高校的科研项目中,人文学科的项目经费也不断增加。但在这些项目所设的类目中,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古籍整理的专类与方向,古籍整理只含在个别大类之中,甚至有的项目明确规定不包括古籍整理与注释等。因此,古籍整理者的项目申请,一般而言,多通过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或者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来申报课题,但后者的经费多以资助出版的方式流向了出版单位,故学者申报多通过古委会来立项,而古委会本身经费有限,又因为涉及全国各地的古籍所与其他单位,因此具体到每个申请者时,其项目经费就很难与国家社科基金等相比。古委会的个人项目少则数千元,多者一般也不会超过3万元。而在这有限的经费中,仅底本费一项就将占去绝大部分。因此,整理者只好放弃对该书的复制。而变通的办法则是:如果该书有其他本子(通常错讹较多),则用之为工作本,校对与迻录善本;如果该书为孤本或与他本相较异文太多,则只能钞录。而这都是古籍整理中最应避免的大忌,因为凡是底本选择不当或者钞录太多,则整理中出现的讹、脱、衍、倒现象也就越多,而这样整理出版的古籍,在点校质量上根本就无从保证。
正因为如此,古籍整理者在选择项目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获得古籍善本的途径是否畅通,按理来说如各大馆中所藏的从未公诸于世的手稿本、稿本、钞本、日记、笔记、档案等罕见古籍,应当优先考虑整理,但各馆中多将此类古籍视为奇货,要价不菲,学者在选择课题时也就往往有意避开这些“硬骨头”,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要复制或者钞录到这些书,有着极大的困难。或者是需要一笔巨额的底本费,或者是像笔者在苏州图书馆所遭遇的一样,即使钞录也不被允许,劳而无功,最终舍弃。因此,还不如不碰为妙。
除了上述诸说外,巨额底本费的收取,还引起了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底本费高,所以整理一部古籍的成本加大,而出版社在影印古籍时,也同样要付大量的底本费,结果就是凡影印古籍,出版后的定价都是惊人的昂贵(当然此不是惟一的原因)。因此,古籍整理与研究者往往处在一种极其尴尬与狼狈的境地,做整理与研究工作时,付不起高额的底本费;而有了好的本子出版,能有机会买书,却因价昂而无力购置。
本来,古籍收藏单位与古籍整理者之间,应该是同根共生、荣辱相依的关系。但是,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如此不景气的今天,古籍收藏单位不仅未能给予古籍整理者以有力的支援与及时的帮扶,反而将其推向更为困惑与狼狈的境地。也就是说,在古籍整理者最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一些古籍收藏单位所做的却是“雪上加霜”。
●古籍收藏制度与规则:不改革没有出路
如前所述,笔者对古籍收藏与利用之关系与矛盾做了种种分析,我相信本文所列的诸种问题,也是绝大部分古籍整理与研究者遇到过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些现象的持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要解决与改革,也需假以时日,但改革是必行之路,不改革则无有出路,至少对读者而言是如此。现将笔者的一己之见述之如下:
第一,在我国各项法律制度逐渐健全的大环境下,现在应该是有关部门探讨与制定一部完整的《图书馆法》的时候了。就古籍阅读与利用而言,我国现行的、各古籍收藏单位自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严重阻碍与制约着古籍的阅读与利用。笔者以为现行的古籍阅览制度,甚至扩大到其他图书的阅览制度,都应该更新观念、大力革新。有关部门应该广泛听取图书馆界、文博系统、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制定出真正能体现保障公众获得资源的现代法规,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读者。
第二,各级古籍收藏单位的上级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对图书馆等建设的经费投入。在古籍与旧报刊杂志的保护上,不应该只把重点放在宋元版古籍上,理想的条件是将大部分的古籍都制成胶卷与光盘,旧报刊复制而存有副本,这样才更利于古籍的保护,也更利于读者的利用。像有些古籍与报刊,完全可以实现网上阅读与利用,使读者既方便又快捷地得到资料。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才能办到的事情。
第三,古籍收藏单位,在观念上应该摒弃旧俗,改革开放。我国许多古籍收藏机构,在观念上仍未完全摆脱古代藏书楼以“藏”为主、限制利用的不良旧习,将古籍视为不可触摸的文物,而忘记了其首先是一部书的基本功能。保护古籍的最好方式,除了制作胶卷与光盘等外,莫如将其整理出版,化身千万,才能长留于天地之间,这才是最彻底、最稳妥、最保险、最高效的保护方式。
第四,古籍收藏机构,应该鼓励与支持对馆藏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学者个人的整理与研究。
第五,古籍收藏机构,应该从埋头在自家院子里的现状中,用开阔的心胸走出去与请进来。可以有针对性地就某些古籍,设计课题,申报项目,与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学者合作进行整理与研究。
拙文并不是要否定古籍收藏单位多年来在古籍的保护与整理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是出于对古籍、图书馆与古籍整理事业的痴心与挈爱,真诚期望传世古籍既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又能各尽其用,古籍整理事业欣欣向荣,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弘扬起到应有的作用。(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漆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