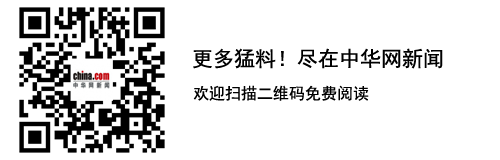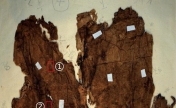炫富,即炫耀性消费,意指富裕阶层通过铺张浪费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财力和社会地位,藉此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
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就讲求藏富不露。因此,这种虚荣示富的行为在当今世代自然被视作祸根,不免会遭到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但有没有想过在400多年前的明朝,这种浮躁消费方式却是文化上最为浓郁的一墨?
明初敦朴之风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一别当初大乱方定,百业凋敝的模样,变得繁华奢靡起来。就连当初以雅为重的大夫们都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再清傲潇爽,甚至争相加入到竞奢大队中。这种靡烂的纵欲之风大抵可以从衣、食、住、行四方面说起。

雅俗并存的衣冠文化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以唐宋礼制为基础,建立了明朝的服饰制度,而这套衣冠制度最强调的就是等级差异。朱元璋希望透过一系列的穿衣规格可以达到“辨贵贱、明等威”的政治功能,不再重蹈前朝“贵贱无等,僭礼败度”的覆辙。只是后来奢风渐递,士大夫们也管不上这些严苛的繁文缛节。在隆庆万历年间,《嘉靖吴江县志》中就有提到:“习俗奢靡,故多僭越。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不能顿革也。”为了在竞商的比赛中脱颖而出,众人的踰制僭越就从模仿帝皇后妃的服饰开始。一些士大夫不仅把国规中的士“顶平定巾”、“衣青直身”弃而不用,改为“峨冠博带”、“方巾彩履色衣”,胆大的不但以天子龙纹、高阶官员的鸟兽饰衣,更是腰金佩玉,导致当时“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朝廷命妇也卷入这奢竞旋涡中,开始穿珠戴翠起来。就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江阴青阳邹令人的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饰、漆器,先不说金玉、翡翠本来就是上品命妇的专有物,当中金满冠上所镶嵌的宝石更不是一个七品官员的妻子可以肖想的珍宝。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广西道监察御史宋蕙墓等一些官员墓葬中也有大量宝石金簪。可想言之,僭越之风在明末期是多么的猖獗。
在以奢为傲的明代社会中,衣服颜色免不了越来越鲜艳浓郁。但是,我们不能以“俗”一字一言蔽之,因为那越趋于豪华繁缛的构图方式亦反映了世人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比如将芙蓉、桂花和万年青绣在衣上,意指“富贵万年”;若将蝙蝠和云霞画在一起,则为“福从天降”。这些衣饰图纹构思巧妙,含义隽永。可见,士大夫竞奢不仅是材质之争,亦是一场雅意之争,毕竟胸无点墨之人实难以体会当中的巧思细意。

色香味俱全的饮食文化
在物资匮乏的明朝初年,饮食文化自然没有多少花样,但到后来社会慢慢富足起来,士人们自然不会委屈自己的肚子,饮食也就越发“刻意求精”。在李乐《见闻杂记》中就有提及张居正吃饭时,哪怕盘上百品菜肴,他仍觉得无下箸之处。至于昊越王妃之兄孙承佑每次宴会都要杀牲纵酒,甚至为了吃到最鲜美的鱼肉,他随车北征也要“以雍驰负大解贮水,养鱼自随”,以便在幕舍中也能脍鱼尝鲜。
当然除了满足口腹之欲,明代士官阶层在追求奢侈中也慢慢重视养生。《读书镜》就有言:“醉醴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虑,无滓无秽。”,所以不少士大夫也会食用蔬菜、粗粮,以促进肠道健康,如兵科给事中蒋性中宴请周忱时,便有碟名为“金花菜”的菜肴,而布政司参政张楚城宴请他人时,亦会在席上多添一道“神仙菜”。虽然只不过是些草头和腌菜,但可以看出士人夫们在竞逐奢华中也讲求修身养性的精致饮食。
明朝之所以这么讲求饮食的精致性,甚至有人大费周章去研究饮食文化是因为文人士大夫看来,吃喝并非俗事。明人好客,多以吃会友,餐宴不仅反映着个人品味,更是促进官场交往的风雅之事。这样看来,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创下“饮食社”,写下《饕史》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富丽堂皇的雅宅文化
在明代,侈丽浮糜之事又怎会局限于衣、食方面,在住宅一事上亦有所体现。江南缙绅士大夫“穷极土木”,就以苏州府城为例,在当时不足二十平方公里之地上,却有园林八十,可谓棋布星陈。当然地皮总有用尽的一天,当苏州府城再也塞不上一座园林时,士大夫们只好改道而行,把消费触觉投放在家俱、字画上
在范濂《云间据目抄》中便有提及“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这些贵巧的名木家俱动辄万钱,可谓靡之极也。除了对家俱有所追求,士大夫亦重视书房中陈设布置更加重视,即装饰品——字画。虽则字画并不实用,可以说是“一趋脆薄”,但观赏时有来的视觉愉悦,以及同侪的钦佩也是奢竞中很重要的元素指标。比如谢肇淛的“小草斋”中便收藏了大量宋版手抄书,而在《味水轩日记》中,李日华也曾多次记载了自己收购书画的记录,以饰其房之事。明人之所以如此重视住宅装饰,很大程度是因为文人常雅集,除了在私家园林吟诗填词,也在在书房中赋歌作画,所以一个典雅的创作环境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虽说很多时候不少士大夫都是附庸风雅,但不可否认书画古董也是竞奢中重要的一环。

排场浮夸的车舆文化
明初朱元璋曾严禁一般官员坐轿,但这种禁令多沦为纸老虎。官绅热衷轿子,只因为坐轿出巡时排军鸣锣喝道,仆人们前呼后拥,而平民百姓们只得在路旁磕头谢罪。这种威风的满足感使不少中央官员外出视察时都向地方强行“索轿”,地方官员自是不敢怠慢,但苦于人手不足,只好让百姓充当轿伕。更甚者,告老还乡时也会要求途经的地方给他大轿伺候,以突出衣锦还乡的声势。比如在嘉靖时期,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赴任时就要求八抬大轿三乘,四抬大轿四乘。前后僱用了三百四十个扛夫和轿伕,从南京到北京就花费了差银千两,派头十足。
袁宏道就曾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归纳明代众生,这也不无道理。从衣、食、住、行我们都能够找到士大夫们竞奢的痕迹,前期激烈无比,针锋相对,但到后期我们往往都可以找到“雅斗”的影子。
可以得知,我们难以用“奢”一字便概括了明朝的炫富性消费,因为不是越贵越好。很多时候,我们都忽视了“雅”的这个元素,因为“雅”总是与“奢”相悖,但正是在明朝,矛盾的两者相生相融,造就了明朝独一无二的竞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