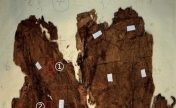就像塞利姆一样,埃尔多安也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让伊斯坦布尔的逊尼派信仰征服世界。塞利姆无情地消灭了他在国内外的敌人,埃尔多安也选择了相似的路线来对付国内的阿列维派信徒(Alevi,土耳其的什叶派群体)、库尔德人、知识分子、民选官员、警察、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记者、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左翼分子,乃至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和平示威者。
因此,借着用塞利姆来命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第三座桥梁,埃尔多安十分明确地拥抱了塞利姆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遗产,这部分遗产也恰好便于他批评凯末尔的共和派世俗主义。如同埃尔多安诸多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政策一样,此举也在土耳其国内外激起了猛烈批评。其中最大的一些批评声音来自土耳其国内的阿列维派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安纳托利亚什叶派信徒的后裔,而塞利姆曾经数次屠杀安纳托利亚的什叶派信徒。因此,冷酷者苏丹塞利姆大桥让许多人回忆起了跨越时代的伤痛、屈辱和暴力,正如非裔美国人和其他许多美国人在面对南方邦联纪念物时的感受一样。而就像南方邦联纪念物的支持者一样,埃尔多安通过命名这座大桥的举动向土耳其国内最主要的少数族群之一传达了一个信息—谁才是“真正的土耳其人”。
埃尔多安此举还意在对土耳其境外的什叶派对手释放信号。他揭晓大桥名称之时,恰逢“阿拉伯之春”。当时,中东地区有数个政府倒台,留下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那几年,伊朗利用自己的核计划来展示肌肉,希望可以使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深入到逊尼派的阿拉伯世界中。为了反制,埃尔多安在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里支持了形形色色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党。埃尔多安为大桥命名的做法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他仍然借此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像几个世纪前塞利姆的奥斯曼帝国一样,今日的土耳其也将是中东逊尼派的坚定捍卫者,甚至还会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使用武力支持逊尼派对抗什叶派势力,与被他视作土耳其的敌人的势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