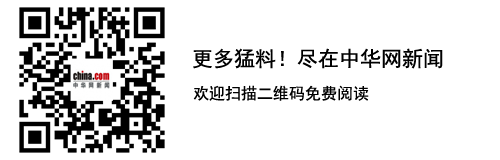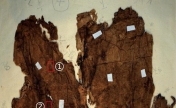简·雅各布斯最被诟病的是她观点的狭隘,城市规划师凯文·林奇将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形容为“一本突出而扭曲的书”,且强烈要求“某种很局限的城市环境”。对于简·雅各布斯过度强调建筑物和街道之类的事物会形塑人的行为,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认为,“简·雅各布斯忽略了带来生命力或者导致枯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使她无视于城市问题更深层的根源”,并且“简·雅各布斯以中产阶级的身份,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西村予以浪漫的投射,忽略了中低收入者生活中的黑暗面”。《美国规划师协会期刊》的一篇评论文章更是指出:“她不接纳不像她理想中的其他城市风格的存在,也不认同它们值得向往,因而落入她自己经常谴责的那种单一思考模式。”有时,简·雅各布斯似乎太急于把传统的学术或专业实践一笔勾销,视之为毫无价值或者更糟。正是通过对这些批评与反对声音的尊重,《守卫生活》完成了简·雅各布斯从“神格”到“人格”的回归。
反思与追问:我们到底在为谁忙活?
《守卫生活》挑明了简·雅各布斯和规划学术界关于城市问题的矛盾点:在1950年代的美国,到底是选择阳光明亮、空气清新、绿地广阔的郊区生活,还是选择喧嚣惊奇、丰富混乱、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这个矛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城市到底属于谁?简·雅各布斯坚决地站在了民众的一边,她努力为深深扎根于城市中的非主流生活方式建立正当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世界并没有按照雅各布斯的设想前进,单一意志力依旧是操控城市的主要力量。因为,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底层逻辑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聚居状态,而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开始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政治性聚居强调尊卑秩序。资本增值则十分强调周转效率,人们被迫卷入一个庞大并抽象的现代化系统,甚至连政治领袖往往也无处可逃。我们到底在为谁忙活?这成了现代性更大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