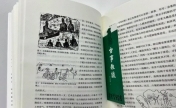元朝的知识分子则不再过问国事,元曲有“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葫芦今后大家提,想谁别辩个是和非”。元代士人不问国事,终日在勾栏妓院中和妓女优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级制度有关。元代的士人几乎是集体退隐。明朝的情况又特殊。朱元璋是个天才,他由一个贫苦的农民、叫花子,依靠士人当上了皇帝,但又总是怀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杀了一批士人,还发明了“批颊”即当面打士人的嘴巴,动辄便把士人打死、掼死,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从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个人只有得到别人尊重时,才能更好地为国为民着想;一个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时,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甚至会毁坏国家、损害他人。所以,历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尽力维护国家,而太监、佞臣等靠自残或迎逢而深居宫廷,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往往就会损害他人、损害国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压政策下,他们不得不为君所用,但也决无发明,仅是虚应故事而已。一旦高压解禁,曾被轻蔑的士人便只考虑个人,而不再考虑国家。当国家危难之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乐年间预修过《永乐大典》的慧暕和尚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乐后期,国家尊重知识分子,对士人采取宽松政策,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还心有余悸,后来胆子大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传播画艺等为名,到国外去定居,在国外搞得好就不回国,搞不好又回到国内来,来去自由。这个时候,慧暕和尚又说:“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二)朱元璋时代,知识分子虽然无负国家,但因心惊胆战,只能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事,个人的才智都没能很好地发挥。到了永乐年间,高压政策解除,知识分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轻蔑又因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大都为自己着想,很少有人愿为国家献身,所以说“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识分子尚能知重名节,而中期至后期的知识分子连名节都不要了。《明史·阉党传》上有一段总结云:“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雠,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最后说:“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诚无所穷极也。”历代的知识分子对阉人是不屑一顾的,而明中期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利益,竟附丽于阉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争献媚”,何其鄙也。到了这一步,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