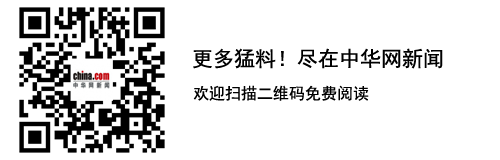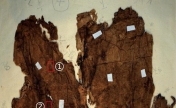我乐于无目的的寻找
新京报:《稍息》是你的第一本摄影集,拍摄的是1981年-1984年的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结集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
老安:对我来说,1981年到1984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有头有尾的时间段。我在那几年一直都是学生的身份。最早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的夏天。当时我还是一名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到南京大学参加一个为期六周的短期汉语学习班。学习班结束之后,我就申请了奖学金,1982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都在复旦大学留学。

在复旦大学留学时期的老安。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毕业之后,我回意大利当了一年的义务兵,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奔波,身份也变化了几次,先是在香港住了几年——虽然我在香港的时候也老往内地跑,但毕竟是住在香港,后来到北京定居之后,因为生活也做了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整体看下来,1981年到1984年是比较整体的,可以被呈现出来的时间片段。
新京报:距离拍摄这些照片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才想要出版它们?
老安:有很多实际的原因。我当时来中国带了很多胶卷,底片也都是我自己冲洗。那几年,我一直都在拍照,冲洗完之后保留了底片,但没有放大。暑假回意大利的时间也比较短暂,没有时间真正去做整理。搞摄影的问题,你也知道,只有到最后整理出来,才知道自己拍了些什么,如果不整理,就会有很多重复的照片。又因为不断有新的刺激,就一直不停地拍,直到自己直觉某一类主题的照片够了,才移到下一个主题。
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我虽然也回来参加了一些展览,初步地整理了一些照片,但都不是很彻底。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到香港工作,我也仍然继续拍照片,再后来又拍视频。但在那个时候,扫描和修图技术都还不是太成熟。我在国内也没有专门的暗房,所以就把整理的工作搁置了一段时间。
当然,我的心里一直都搁着这个事儿。到了1993年,我又拿了一些之前放大的底片出来,和我的好朋友、摄影家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次展览。这应该算是这次出版前唯一的一次公开。

1993年,老安与奥利沃·巴尔别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摄影展览《两个意大利摄影家在中国》。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这次回头挑选照片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
老安:挑选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过程,找回了很多我早就忘掉的记忆。说实话,隔了这么多年,很多照片你要说是别人拍的我都信。包括有些照片我甚至都忘了是在哪里拍的。(笑)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前后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挑选照片。一会儿加一张,一会儿又减一张,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律和标准,硬要说的话,就是我自己认可的,放出来也不丢人的照片。
新京报:你说到没有明确的规律和标准,这也是我的阅读感受。整本摄影集完全没有主题,也没有分地域,就像是透过照片在不同的城市里漫游。
老安:对。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想要描述某一个地方或某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吸引我,或者我觉得有点儿意思的,我就拍。
新京报:这是否和你对摄影的理解有关?
老安:是的。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摄影史的视域里看,我最早接触摄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视觉艺术刚开始兴盛起来的时期。当时我喜爱的摄影家,包括意大利的奥利沃·巴尔别里、路易吉·吉里,美国的伊文思、Lee Friedlander,法国的Eugene Atget等,他们都不太关心特别壮观的东西,而是关注大环境的变化、大部分人移居的城市郊区、人工照明与广告的介入等边缘主题。

意大利摄影家圭多·圭迪的摄影作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