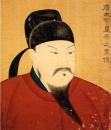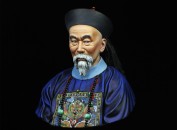然而,自以为王师所向便无往不利的姬瑕,显然低估了战争的残酷。周军在进入汉水流域后很快便遭遇了虎方及当地部族顽强抵抗,以至于大军渡过汉水之后根本无法立足,最终不得不通过浮桥狼狈北逃。然而,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不知道是因为事出仓促、工程质量不过关,还是遭到了虎方的秘密破坏。总之,在姬瑕与祭公、蔡公等核心成员所在的中军先行通过时,整座桥梁突然垮塌。
由于事发突然,常年养尊处优的姬瑕等人当即便沉入水中,虽然以辛余靡为首的一干近卫侍从拼死抢救,但却也仅仅打捞出了三人的尸体。按照常理而言,天子落水而亡,身边的扈从难逃保护不周之罪。然而,由于浮桥断裂,周军后至的野战部队悉数被困在了汉水南岸,几乎全军覆没。在如此空前的惨败之下,侥幸保护着姬瑕遗体逃回的辛余靡自然也就成了有功之臣,受到了“侯之西翟,实为长公”的嘉奖。
可能是周王朝讳言失败,更可能是因为没有太多幸存者可供回忆和讲述。总之,周昭王姬瑕的第二次南征并没有留下太多可信的历史记录。反倒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民间传说大行其道。如所谓姬瑕是误乘了被人动了手脚的“胶舟”,便可能是对由船只连系而成的军用浮桥的误解。
从结果来看,周昭王姬瑕的死亡虽有其个人性格上的必然性,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毕竟此时依旧强大的周王朝真正要全力以赴,并非不能征服汉水流域。据说姬瑕之子穆王姬满执政时期,周王朝便曾出动庞大的地面部队,以形同鼋鼍的战舰组成的浮桥,一举越过了长江,击败了九江地区的越人。
但是那样畅快淋漓的复仇,要等到姬瑕去世后的第37年年头。在此之前,为了牵制虎方,周王室授意楚人在新生代领导者熊渠的领导之下,由周王朝指定的国都丹阳,举国迁往“发渐”。尽管“发渐”这个地名除了《楚居》之外,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献史料之中。但根据近代湖北枝江地区曾考古发掘出的西周中晚期楚国编钟来看,熊渠此次迁都的目的地,很可能便是汉水以南的宜昌、当阳、枝江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