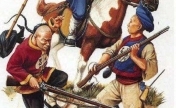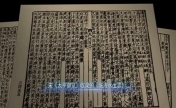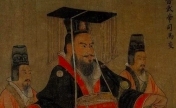陆战首战成欢之战时,清军到达朝鲜的兵力不及日军机动部署兵力的一半,首战即寡不敌众,对后续入朝部队的兵心士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平壤之战前夕,清朝才急忙急脚地大量招募新兵,充实兵力,这些新兵连开枪开炮的基本的训练都没有时间完成,作战表现不难想象。平壤之战爆发时,清军本应运抵前线的大量后勤物资还滞留国内,成了平壤守将不敢与日军相持的重要原因。
二、内部派系林立,互不支援
战略指挥应该做到的高度集中统一,由于清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军队又派系林立,清廷根本就做不到,在战场上多次形成了日军力量集中,清军力量分散的不利局面。
鸭绿江之战,因为作战部队来自于八旗练军与勇营两个系统,清廷只好将防线一分为二,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四川提督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分别负责。
山东半岛作战,清廷在同一战场上委任了两个战区指挥官,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海军基地威海卫防卫,其它陆上作战则由山东巡抚李秉衡调度。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政敌,对李鸿章护卫后路的支援要求各种敷衍拖延,很有作壁上观的嫌疑,导致威海卫守军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独自与优势兵力的日军对抗。
在战争期间,由于李鸿章、刘坤一等战略指挥员信心不足、军队野战能力差、战术战法保守等原因,清军实际上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违背了战略指挥应牢牢把控主动权的基本原则,一再在战场上陷入以寡敌众或坐困危城的被动局面。
在朝鲜战场上,李鸿章要求“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入朝各军听令株守平壤孤城,不主动出击,将战场主动权拱手让与日军,在后勤不继的情况下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
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战法,完全没有集中必要力量实施机动阻击的布置,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是必然结果。且淮军是李的私家军队,对军阀来说军队是其根本,没有了军队也就没了一切,观淮军的表现大有弃地保军之嫌,因而才会有一触即溃或者望风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