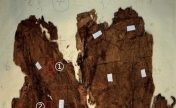周人崇祀天神,山岳为天,实际上就化崇天为山岳崇拜。周人始崇岐山,随着东迁转为嵩山,认为嵩山为其祖先神群居之处,且将其山巅名曰“天室”。西周至春秋时期嵩山地位最高,但张富祥认为嵩山“显见是受到东岳泰山文化的影响”。至战国,随着周王室的衰落,齐鲁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嵩岳的地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东方的泰山。
值得一提的是,商周之时神权观念的变革对山岳祭祀乃至审美的长远影响。《礼记·丧记》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周人初承殷礼,嗣后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原始文化上升到了治国纲领的高度,成为上下的行动指南,形成了尊天、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观,并渐成轻神重民、以民为本的观念,从而为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至春秋战国时代,“天地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不再被垄断。儒家弟子所记载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称“太(泰)山之高,参天入云”,意义非凡:客观上看,其时泰山已成为非祀可登、可审美抒情的场所,而不是纯粹的神灵所居的天室,打破了商代或类似欧洲中世纪前的山地上下“人神二分”的观念。与欧洲相比,中国人把山地作为审美对象早了两千年,应是这类“思想解放”的延伸成果,深刻影响和丰富了中国后世独具一格的山岳文化,堪称泰山名山文化建构的原点。
(三)秦汉时期:泰山首山地位奠定
泰山地位的奠定,嬴秦人当为首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起于泰山山脉东缘嬴汶河流域的嬴姓一族,商末周初有记载的至少三就有批嬴秦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西部,其中包括清华简上记录的周初三监之乱时被废姓绝祀的一批嬴秦族人:“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朱圄,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