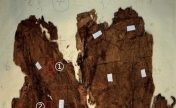当然,始皇的泰山之行,也要看到另外两个重要诉求,一是国家安全的需求。这当是源自于人类的心理需要,也应是一国一朝的第一需要。国必定四至,而“四岳”“五岳”则为领土四至的象征物,也体现了地处中央者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是需要时时维护的:长城的修建、四塞之地的追求、重兵的驻守、帝王的不断巡视当是安全需要的必然行动。《尧典》《舜典》所载的尧舜岁巡“四岳”,与其说是泽被四方,不如说是对领地完整安全的再确认。“一家天下,兵不复起”(峄山刻石)、“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琅琊刻石)、“登兹泰山,周览东极”(泰山刻石),从秦始皇东巡的上述纪功刻石看,正反映了此类诉求。二是宣示一统天下。泰山是“东极”的象征,是战国盛行的五行说中化生万物之所在。泰山之所以具备一统的标志性,就是因为其地处东极,对地处西部的帝王而言,一旦东极在手就代表着天下统一。
对登封泰山而言,登临一次而多附加几层内涵,让帝王登山的仪式感更强烈、意义更为博大、皇权更加神圣,也一并展示一下齐鲁大地文化重心的地位,彰显一下能影响帝王的话语权,于各方均为共赢,何乐而不为?而对始皇而言,心底里或许还满足了嬴秦一族“衣锦还乡”之愿。
可以说,上古传统、疆土一统象征与战国时期五行说、封禅说等共同建构了泰山首山地位。有无嬴秦荣归故里的愿力尚无从考证,但能在秦人身上实现泰山封禅,从中至少也可以看出稷下学宫身后的影响力,更见识到儒家一派神道设教的政治手段。至于后世所言始皇与儒家的过节本文不议。刘宗元认为,嬴秦一族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推动者,而泰山就是重要的见证者。与此同时,始皇还给后世开启了谈论泰山的新角度:谈泰山不谈一统,与谈一统不谈泰山一样,都未触及泰山精髓——华夏一统、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