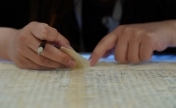毓坤会主办者和授课内容均没变动,唯有开办地点已具体选定了“三海”(南海、北海、中海)中的南海,汉族女性的入学门槛也由“五品命妇”提升至“三品命妇”。课程中开设“各国语言文字”,大异于传统宫廷女学,颇具有现代意味,其实是与主办者的个人趣味有关。1903年的《大公报》称,“裕朗西之女公子,颇得皇太后欢心,不时入内,二人皆衣洋装”。二人即是容菱(1882-1973)和德菱(1886-1944),通英、法语,曾在清宫中担任翻译,颇为慈禧宠爱。而且,在议设毓坤会后不久,容菱、德菱及其母亲又拟设八旗女学,“专收旗民幼女,以期培植女才”。以德菱姊妹主持毓坤会,可谓无二之选。
就在北京女界和报界翘首期盼中,毓坤会却迟迟未见下文。直到次年初,据《警钟日报》透露出来的消息,毓坤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乃是因为慈禧对女学的看法出现了变化:
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暗;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京师则尤甚,有无关系者均视作密切问题。俄使更番警告,联派党咸有戒心。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德[听]。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星期出游,亦甚寥寥。西后因学堂迭现怪象,意滋不悦。前拟设毓坤会兴女学,亦中止矣。
消息中所涉先后事件,指1903年春开始兴起的“拒俄运动”、1904年秋冬在长沙流产的华兴会起义以及当年11月上海发生的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前两事,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都充当了中坚力量,因而清政府对在校学生的日常活动极为警惕,极易产生过度反应。再加上近臣对当前男女学堂的大小“流弊”的渲染,动摇了慈禧对于女学的热忱,毓坤会之事也就意兴阑珊了。
1905年5月《大公报》又有“毓坤会”的消息,但记者语气已经十分犹疑,在按语中言,“上年即有此等传说,究竟不知确否”。事实上,德菱在两月前赴上海照看病重的父亲,离开了清宫。从此在《大公报》上,再无毓坤会的消息。